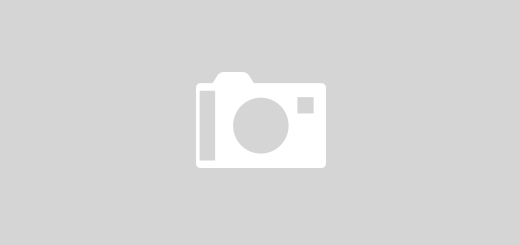网络日记:读《寻找如画美》……
读《寻找如画美》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想起我自己写过的一篇文章《我怎么看到风景》,文章是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风景,有的人看到风景很美,而有的人却觉得索然无味。对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很久,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有的人具有一定的审美观点,而有的人没有,那恐怕不能让人信服。我在文章中写到了我外婆,一位根本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村老太太,在文革动乱的时候,我父母亲被关押了,她把我带到靠近长江边的乡下,外婆经常带我去长江边的一座小山上看江边的风景,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外婆喜欢到这里来看啥,尤其是夏天,还有蚊子叮咬,秋天还有些凉意,她也经常带我去。几乎每次去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在我的眼里,无非就是江面的船,以及远处的太阳或者月亮,再就是太阳或月亮周围的云彩,外婆看风景的时候看得很认真,她能辨认出江上行走的船是什么船,客船还是货船,如果是客船她会知道这班船有可能是从哪里开往哪里去的,如果是货船,她能知道船上大概装的什么东西,或者是空船。看远方的太阳、月亮或者云彩,他会给我讲出很多故事来。那时候的我,真的很佩服我外婆,外婆她虽然出生于有钱人家,但她确实没有多少文化,如果说有一点的话,也就是她能看书,却写不出字儿。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外婆怎么会看得懂那么多风景呢?而别人家的爷爷奶奶为什么不会到这山头上来看风景呢?
后来我想,我们怎么才能看到风景呢?其实这个答案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的心中如果有风景的话,你到那里都会看到风景,如果你心中没有风景的话,即使再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
而〈寻找如画美〉书中更主要的还是认为::“一个精通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和维吉尔作品的人要比一个门外汉更能品鉴出田园风光的味道。”这点,我很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难道除了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和维吉尔就没有人更理解田园风光了么?我相信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和维吉尔对田园风光有一定的研究和认识,可是别人也会有更多的研究和认识啊,譬如我外婆,她对长江水边的风光或许有其特别的认识和感受,这种认识和感受或许是别人无法企及的那种。可是,话又说回来,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岸边又有多少外婆这样的老人呢?而他们每个人又会有多少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呢?住在长江下游两岸的和住在长江上游两岸的,他们的认识和感受会完全不一样,甚至住在长江南北两岸的人,对他们所见的长江风景也会有不同的感觉和认识的。这又会让我们看到,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所看到的风景,都会不一样。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一个看风景的人,心中必须有他独特的风景所在。
以下是《寻找如画风景》的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如画美的兴起
第一章 诗歌与英国风景之发现
画境游的本质是一系列悖论。这里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两个开始。第一个,游客想要发现未经人类触动过的大自然,但是,一旦发现了这样的大自然,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要去“改善”它,哪怕只是在想象中。第二个,在湖区和威尔士北部到处旅行的游客会比照理想化的外国模式,罗马田园牧歌或者17世纪的克劳德和萨尔瓦多•罗萨的绘画,来高声赞扬英国风景的天然之美。二者在此相互关联:“改善”的冲动得之于一种教育出来的意识:是什么构成了理想的风景。面对大自然而产生的两种反应,其悖论的本质并未使游客感到困惑,对他们来说,习惯性的比较和联想提升了他们对于自然美景的体验,就这么简单。一处威尔士山谷如果看起来与加斯帕.杜埃的画作逼肖就会获得很高的美学价值。初次看见一位坎伯兰牧羊人领着他的羊群攀上丘原,此番情景越与文学原型接近,越能令人兴奋:突然,维吉尔的《牧歌》若隐若现于游客与牧羊人之间。甚至一处工业化的景象也会变形,一位同时也是牧师的游客在丁登寺时就透过客栈的窗户目睹了河岸边钢铁工厂的熊熊火焰,他说道:“我们目睹维吉尔的描写成为了现实,埃特纳火山的内部,独眼巨人的熔铁炉,他们令人生畏的工作,一下子涌入我们心头。”无独有偶,在18 世纪70 年代初期,面对曼切斯特的煤坑,一位诗心盎然的游客诗兴大发:
这新奇的景点怎能不叫我回想
那些古典寓言,我们曾被教过;
那些古老的神话,我们曾经学过
老卡伦的渡船,冥河的波浪。
于是,文学教育成为了带进田野的额外又昂贵的智力装备,并发展出阿契巴德•埃里森所说的“欣赏风景的一种新意识”:
……也许大多数人都会回想起:当自然开始呈现出别样的风貌时,正是他们沉浸于古典文学的学习之时。对多数人来说,至少,诗意的想象最初出现在求学阶段。古典诗歌的描写推动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识,凭着这一意识他们能够看见自然的面容。
有鉴于此,比起没有文化的观景人,画境游的游客就有了更多的美学特权,正如理查德•佩尼•奈特在1803 年所评论的那样:“一个精通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和维吉尔作品的人要比一个门外汉更能品鉴出田园风光的味道。”c如果古典诗人换成了画家克劳德和罗萨,这一观点依然切中肯綮。画境游的游客,至少是如画美旅游的第一代,都是鉴赏者,都受过古典文学的熏陶,熟悉克劳德、杜埃和罗萨的画作。一个鉴赏者,按照18 世纪的严格意义,就是一个“有趣味的人”(a man of taste),约翰.克莱尔就使用了这一称谓。尽管社会背景与鉴赏精英阶层的相当不同,他却用同样的词汇以示甄别:
每当一处自然的景物令我想起我喜爱的一些作家所描写的诗歌意象时,我总会欣喜不已,……一个小丑也许会说他喜爱清晨,但是一个“有趣味的人”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感受清晨,他不禁想起了汤姆逊的美丽诗句“柔眼的清晨,露水的母亲”。
“有趣味的人”和“小丑”这样的区别生动地说明了如画美的精英主义倾向。旅途上这两类游客经常狭路相逢,衣冠楚楚的游客拿着速写簿和铅笔蹲在溪流之中,打量着一个呆立在瀑布旁的湖区牧羊人,试图找到正确的角度去画下眼前这足以令罗萨嫉妒的一幕。这种可资比较的邂逅得到了富有象征意味的表现,我们能从约翰•普劳的《乡村建筑》(Rural Architecture,1794 )一书的蚀刻凹版扉页中窥见一斑。在温德米尔湖岸,着装雅致的游客、有趣味的人物正把乡村的素朴之美引入人手巧饰出来的自然景观之中—温德米尔湖百丽岛上新的古典风格别墅(普劳设计)。乡村的素朴误被表达得高深莫测,意在传达知足之乐。
本章论及风景诗,我有两个目的。第一,说明一个“有趣味的人”应该从想象性文学中获知的知识:乡村生活的诗歌,大部分遥承罗马诗人,游客就是根据诗歌所提供的理想化模式来评价英国乡村生活和景色的;第二,指出英国诗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推翻或归化几个著名的文本中的古典主义模式—此举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我将其称为英国风景之“发现”。18 世纪中期,希腊罗马文化权威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古典主义诗歌中加进了英国本土的风味,诗人尝试使用本土的传统,哥特风和凯尔特风大行其道,而恰在此时,英国画境游开始兴起。从许多方面来看,画境游自觉地继续了这一文化自我定义的过程。
第一节.乡村生活种种
当我才思枯竭,耗尽了我那点情感、评论或描写的存货,我转向诗人寻求新鲜的、而且的确更为丰富的供应。……简言之,此处[高地之旅的一处]除了没有一位阿敏塔斯(Amintas )之外,什么都不缺,足够让我想象自己身在阿卡狄亚(Arcadia)。
这番引自玛丽•安•汉威1775 年旅行日志的奇思怪想,典型地说明其时的游客如何乞灵于牧歌来想象自己置身在希望的风景之中,将眼前的景色与诗人(特别是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所描写的牧歌意象联想起来。用来描述18 世纪早期英国文学的“奥古斯都”(Augustan )一词指的是像蒲柏这样成就裴然的作家的创作方式:他们有意识地模仿在公元前1世纪的凯撒•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大领风骚的拉丁诗人。对这一文体的虚假性,后来的奥古斯都牧歌诗人都非常清楚。他们知道自己时代的牧羊人与理想化的文学范型几无共同之处,他们自己也与牧羊人的世界毫无干系。查尔斯•杰纳在他的讽刺诗《城镇牧歌》(Town Ecologues,1723)中直截了当地呈现了两个世界的割裂,他想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几大牧歌诗人,蒲柏、安布罗斯•菲利普斯和约翰•盖伊:
在泰晤士平坦的岸边,他们把乡村之歌构想,
在簇簇灌木丛里,他们自在地徜徉;
青青草地,花儿芬芳,他们精挑细选,
在孤寂中写作,与贵族们寻欢。
牧歌是一种方式,借此人们可以想象自己逃避都市或宫廷生活的压力,躲进更单纯的世界之中,或者也可以说是躲进一个苦心孤诣构想出来的、与城市复杂的社会形成对照的单纯的世界里去。如果那些怀着同样的兴致的18 世纪游客在出发前往北威尔士或者湖区时也会像玛丽•安•汉威那样按照牧歌的套路来设定自己的预期,那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呢?即使按佩尼•奈特的话来说他们不“精通忒奥克里托斯和维吉尔作品”,他们也会知道一整套英译古典文学—从德莱顿的维吉尔译诗到一大串的英语牧歌,或者是略窥过詹姆斯•汤姆逊、歌德斯密斯和其他诗人作品中的牧歌世界。就是略窥,也够游客一用的了,因为这些作品,用蒲柏的话来说,“提供了他们所谓的黄金时代的意象”,这个时代永在春天里,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发现存活在英国偏远角落的黄金时代的和谐—在此渴望的鼓动之下,游客们忽视了牧歌生活的现实。有处景色最能说明黄金时代的和谐,就在格伦克鲁,通往罗蒙湖(Loch Lomond)的山隘,威廉•吉尔平和多萝西•华兹华斯都曾为之倾倒。请看吉尔平的描写:
山谷中间有所孤零零的茅舍,掩映在几棵大树之下,有个小小6 的果园,几间杂屋。我们可以称它就是一个帝国,乡下人安居于此,管理着他的牲畜,一群群的牛羊在丰饶的山谷中啃着青草。他卑微的住所笼罩在和平和宁静之中,若不这样,它怎么可能与周边的景色浑然一体?
未做任何细查,吉尔平一带而过,欣欣然于自己的牧歌想象。将近三十年之后,另一位游客来到此地,好好地探究了一番他描写过的茅舍。它占地大约长27 英尺,宽15 英尺,分为大小两间,大的养牲畜,小的住人。屋主一家靠养奶牛为生,年收入15 英镑。这位游客想起了最著名的牧歌抒情诗中的一首,即马洛的《激情的牧羊人》,两相对照,她被那位母亲憔悴的面容吓坏了:
……她周身的一切都充分地证明(假如证明是必要的),尽管有着“山丘翠谷,溪涧田野/ 崎岖蜿蜒的群山”所能给予的一切愉悦,牧歌生活是那么的贫穷悲惨,毫无诗人脑袋发昏臆想出来的阿卡狄亚的欢乐可言。a
黄金时代的牧歌服务于怀旧和乌托邦的目的。怀旧牧歌的感情冲动与对儿童时代理想化的记忆有关,冷静靠谱的塞缪尔•约翰逊在《漫步者》(Rambler)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散文(1750 年7 月21 日)中如是评论道:
[牧歌]展现了一种生活,我们已经习惯将它与和平、闲适和天真联系在一起。……童年时代,我们想到乡村,认为乡村属于快乐之地,到了老年,我们重回乡村,认为它是安息之地,也许还带着些间接而不确定的快乐—每个人回顾那些地方,或者记起那些构成他年轻的享受、带他回到生命美好阶段的事件时,就会感到这种快乐,那时节的世界满是新奇欢悦之事,他的周围一片欢声笑语,希望在他眼前熠熠放光。
如果诗人所谓的童年天真和牧歌一样的黄金时代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不可复现于世,那么对于越来越富裕却又厌烦城市的奥古斯都人来说,他们还是有可能享受乡村退隐之乐而又不弃绝文明生活之种种舒适。正如风景中的牧羊人激发人们联想到维吉尔式的牧歌生活一样,宁静地栖居在乡村这种生活有着悠久的古典原型,它在贺拉斯《长短句集》(Epode)的第二首里就能发现。17 世纪,这首诗被人翻译的次数最多。抒情诗赞美人的乐天知足,他安于乡村生活,隐居在他小小的家庭农场里。就此而言,亚伯拉罕•考利的翻译最为到位:
幸福的人啊,博爱的诸神允诺他
用自己的双手耕作祖传的土地!
犹如黄金时代的凡人那样快乐
他摆脱了凡俗之事和对金钱的忧虑!
贺拉斯式的牧歌明显地表达出对黄金时代的向往以及使向往成为现实的努力。幸福的人在他的小小农庄里劳作,照管他的葡萄、羊群和蜜蜂(自给自足,而非拿到市场上牟利),大自然慷慨地给予回报:
他是多么幸福啊,人在浓荫里
古老的树木紧紧庇护着他,
头枕鲜嫩的青草,他无忧无虑,
心无牵挂,也无害怕。
对于王政复辟时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人们而言,自给自足的农庄生活那种境界太难达到了(原抒情诗里那位放高利贷的人奥菲尔斯的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离城市不太远的一处乡村别墅是贺拉斯式理想更可取的形式。18 世纪最受欢迎的诗歌之一,约翰•庞福瑞特的《选择》(The Choice,1700 )深情款款地描写了这一理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蒲柏的父亲从伦敦搬到挨着温莎森林的宾田(Binfield),开掘了一处小小的园圃。宾田庄园以及蒲柏自己的河岸别墅都在特肯汉姆(Twickenham )乡下,这两处算得上是贺拉斯式乡村隐居理想的翻版。在他人工开挖出来的洞穴上方,蒲柏镌题下他的文学灵感、贺拉斯的诗句:Secretum iter et fallentis semita vita (曲径幽处,仙境可期)。
18 世纪末期,道路体系有所改进,人们能够到离都市更远的地方建造乡村别墅。的确,寻访如画美有时候相当于勘查贺拉斯式的隐居地。许多有钱的北方工业家喜爱乡村生活,于是就在湖区风景优美之地置业,改建老式的茅舍或者建造新别墅。丁尼生的•《埃德温莫里斯》(Edwin Morris,1835 )就记录下这种变化:
当时,我是一个速写画家:
看这里,我画的:山岚、小桥的曲线,
……城堡的废墟……就在岩石之巅
看起来就像岩石的,是青苔覆盖着的炮塔;
再看这里,古老地方的新贵,
他们是百万富翁,来自默西河那边……
新居民对“能看到风景的产业”求之如渴,对此华兹华斯深感悲哀,因为所谓能看到风景的产业意味着他们的房子必须矗立在能够纵览风景的光秃秃的山顶上,这样“就和周围隐在林丛之中的老房子形成刺目的对照”,也和山谷居民的茅舍形成刺目的对照。
乡村茅舍逐渐发展成为英国最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建筑形式,被用于表达贺拉斯式的理想。乡村宁静生活的象征,古老的“寒舍”(humble cot )把牧歌情调和贺拉斯式追求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田园景象,
我近日看见一处茅舍,住着乡里郎;
那么整洁,那么隐秘,那么静谧,
看起来一派清真,格外安详……
朴素大方,不炫耀
海外的奇珍装点出金碧辉煌;
茅草编就的栅栏,覆盖的屋顶……
仅能把冬日的寒风抵挡,
却和阿卡狄亚牧羊人古老的寒舍一模一样。
太多的联想附着于乡村茅舍了。茅舍就地取材,非常质朴,与用进口材料建造出来的帕拉迪奥式豪宅泾渭分明。当时,很多有钱的企业家,他们会在自己的庄园里建造一处茅舍,作为意趣和志趣并存的园林建筑的一部分。威廉•马肖在他的《种植与装饰性园艺》(1785 )一书中论及“装饰性茅舍”和“每个部分如何呈现出纯洁和朴素之美”时,建议引种的花卉“应该产自本地”。b在现代的游客眼里,正如在18 世纪的游客眼里一样,古老的、不规则的、茅草覆顶的屋舍代表着如画美,令人愉悦。“简单生活”(a beatus ille)渐成风尚,流行开来,佩尼•奈特在他的《风景》(1794 )一诗中如是写道:
不使人嫉羡,在他寒微的地盘,
坐落着一处隐居之所,茅舍古意盎然;
屋顶覆着野草,点点苔痕弥漫,
忍冬花缠绕门的四周;
青青长藤沿着墙壁攀援,
直到烟囱的上端,茵茵一片。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
本文标题:
文章链接:club.fxplus.cn
文章来源:分享日记
友情链接:✅女娲导航 ✅恋爱之书 ✅健康笔记 商务笔记 ✅健康杂志 ✅分享笔记 ✅健康社区